對舊制度舊倫理的批評乃是譚氏倡建新制度新倫理之先聲。譚氏社會思想的基本點有二:一是倡“民權”,二是倡“平等、自主”的社會倫理。
關於“民權”,譚氏有謂:“生民之初,本無所謂君臣,則皆民也。民不能相治,亦不暇治,於是共舉一民為君。夫曰共舉之,則非君擇民,而民擇君也。夫曰共舉之,則其分際又非甚遠於民,而不下濟於民也。夫曰共舉之,則因有民而後有君;君末也,民本也。天下無有因本而累及本者,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者:夫曰共舉之,則且必可共廢之。君也者,為民辦事者也;臣也者,助辦民事者也。賦稅之取於民,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。如此而事猶不辦,事不辦而易其人,天下之通義也。”這樣的觀念已大大超越了前述“民權論”。歷史地看,它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份子所能達到的對“民主”的最完整的認識和意識。“民擇君”的思想類似於盧梭的“社會契約論”,而“民本君末”的觀念則無疑來源於民本主義傳統。這些主張離邏輯地導出“人民主權”的觀念已經不遠了。同時,在《仁學》中我們可以看到,法國大革命給譚氏以深刻的印象。針對中國的現實政治,他主張通過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,徹底剷除君主專制制度,建立“民主國”。譚氏的思想代表了“變法”走向革命的過渡。他的“革命”思想令人想起了孟子對“革命”的認同以及盧梭對人民有權反抗壓迫的論證。
關於平等、自主的社會倫理,譚氏以為,只有以人人有“自主之權”為前提的平等,才是人類關係的規範,根據這一規範建立的人與人的關係才是自然的、合理的。因此,譚氏認為在傳統的人倫關係中,只有朋友一倫才有存在的合理性,“五倫中於人生最無弊而有益,……其惟朋友乎”。“顧擇交何如耳,所以者何?”一曰“平等”,二曰“自由”,三曰“節宣惟意”。總括其義,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。譚氏進而提出應以朋友關係所體現的“平等”、“自由”的原則改造全部人類關係。他要求廢除“三綱”,所有的人類關係皆以“朋友之道”貫之。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,譚氏達到了一個重要結論:“今中外皆侈談變法,而五倫不變,則舉凡至理要道,悉無從起點,又況於三綱哉!”即是說,倫理革命是社會變革的起點。
申言之,中國社會要向現代化轉化,應始自支撐它的價值系統的轉換。因為一個社會的倫理規範是該社會價值標準最集中的體現。十分清楚,對譚氏而言,新的價值標準就是“平等”與“自由”。
3.新民——梁啟超
梁啟超(1873-1929)的“新民”學說是中國近代人權思想的綜合。我們已經知道,康有為發現了人類個體的自然存在及其意義,嚴複與譚嗣同則分別確定“此人”應當是“自由”和“平等”的。現在,梁氏斷言,正是“此人”才是社會和國家的主體,其恰當的名字叫“新民”。“新民”的“新”,作為形容詞,乃是與中國傳統對比而言,傳統中國只有臣民或奴隸,而無獨立自主的現代國家的“公民”;作為動詞,根據梁氏,那就意味著對傳統的中國人進行根本的改造,變臣民為國民,變奴隸為獨立自主的個人,變傳統的中國人為現代的中國人。梁氏塑造的“新民”形象是:具有獨立人格,享有自由權利,富於創造精神,擁有社會公德。
梁氏和康有為、譚嗣同、嚴複一樣,一直關注著在西力衝擊下的中華民族的命運。追求國家的復興,無疑是梁氏運思的主題。《新民說》代表了他進行這種思考的最嚴肅的努力。
梁氏對中西文明的觀察所達到的認識,頗類似於嚴複。在他看來,中西之間的差距,決不僅僅是科技文明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差距,在科技和制度之外,還存在著一種更為根本的差距,即是:西方國家有公民而無奴隸,專制的中國則有奴隸而無國民。國民與奴隸之區別在於自由的有無。西方諸國勝於中國者,乃因其有自由的國民。梁氏認為,在中國,如果不從改造國民入手,使人民從奴隸變為自由的國民,而困於科技的引進,或汲汲於政體的轉型,推行議院制度,不但收效甚微,而且是極危險的。同時,進化論,特別是斯賓塞發展起來的社會有機體學說,也使梁氏相信,國家的競存能力來源於構成這一整體的成員,國家的強弱全系於他的國民的素質。中國貧弱的原因,在人民缺乏自由,沒有獨立自主的人格,在民力、民智、民德諸方面均較西人為差。而值此?國並立,弱肉強食、優勝劣敗之時代”,要拯救危亡的祖國非“新造吾國民”不可,這便是結論和出路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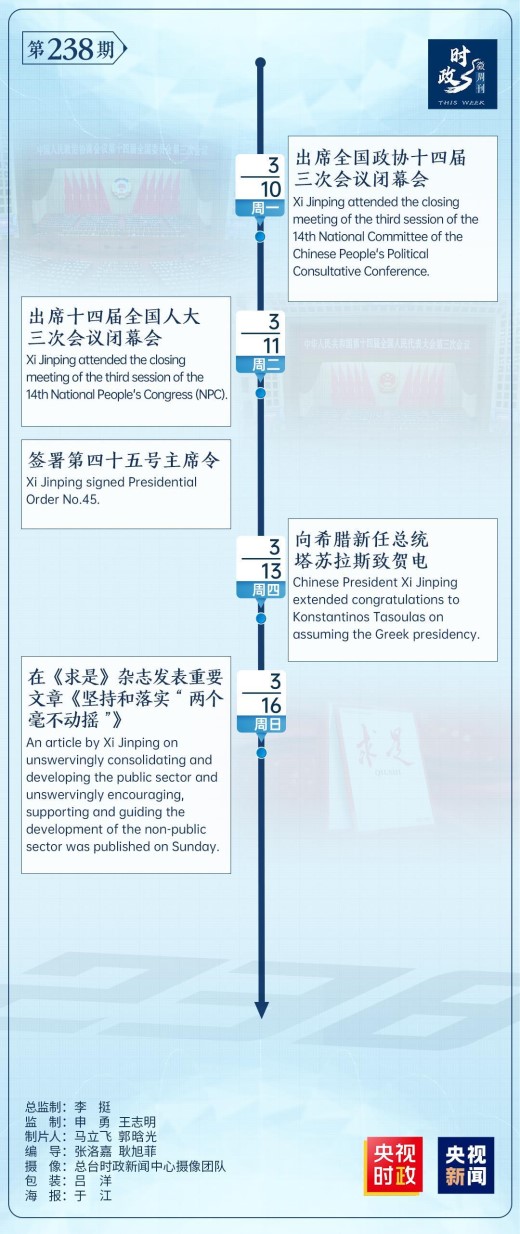


請先登錄再提交評論